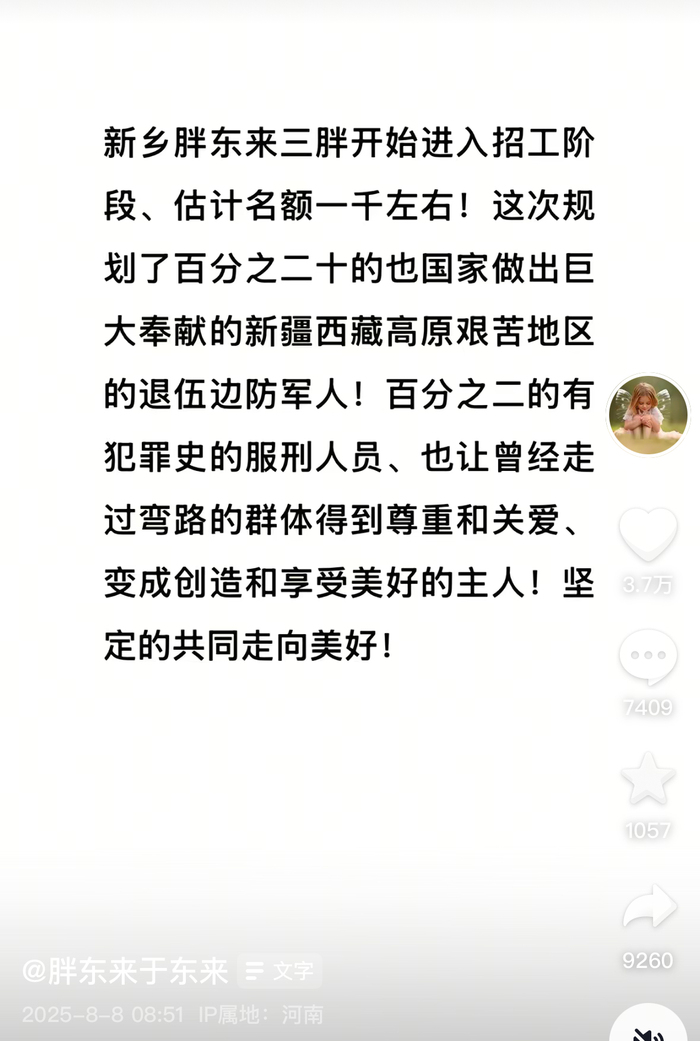王笛:建构微观历史中的边缘者叙事
什么是微观史?
微观史是什么?这是讨论这一领域时无法绕开的首要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微观史不是一种被普遍认同、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不构成一套统一的理论范式。微观史更像是一种不断发展和转化的研究传统,既非单一的视角,也非固定的技术。用更贴切的说法,它是一种历史观的转向,一种特定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细小的对象、边缘的视角和日常的细节,观察宏观社会的运行逻辑。
我将结合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茨堡最新中译本《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下文简称《线索与痕迹》)和我自己刚出的《中国记事(1912-1928)》中的研究成果来现身说法,探讨微观史如何通过“边缘线索”来发现扑朔迷离的、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卡洛·金茨堡著《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鲁伊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版
卡洛·金茨堡作为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未宣称自己的研究是“微观史”,他只是将其视为“历史小切面的放大研究”。对细节的执着,正是微观史与传统史学之间最显著的差异。而我认为,“微观史”就是“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它需要具备两个要点:其一,要有细节,要有故事;其二,研究对象必须是那些“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边缘人物而不予理睬,甚至通常全然无视”的普通人,是“那些被迫害的和被征服的人”。
为什么要讲“边缘者叙事”?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史家关注的更多是国家、战争、王朝更替,主角是将相王侯、革命英雄、大人物。而微观史则不然,它专门把目光投向那些历史舞台边缘的小人物、小事件、小空间。它相信,在这些被边缘化、被遗忘的个体身上,同样蕴含着深刻的时代信息,甚至有可能揭示主流叙事所忽视的张力与裂痕。
我们今天熟悉的“大历史”,往往是由少数掌权者书写的,是胜利者的记忆,是主流社会的自我表达。可在历史的背后,还有无数“没有名字”的人:农民、磨坊主、街头艺人、茶馆老板、妓女、拾荒者……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宏大叙事中极少出现,甚至被彻底抹除。
微观史并不只是关注“边缘人”,它更关心的是: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外,是否存在另一种观看的可能?是否可以不从上而下地解释历史,而是从下而上、从细微处捕捉历史真实的质地?
因此,微观史不是宏观史的对立面,而是其补充与批判者。它通过将“放大镜”置于微小之处,重建那些被主流历史遗忘或压抑的经验。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写的博士论文是成都街头文化,也正是通过微观的切口,揭示城市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生存的挣扎。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接触金茨堡的微观历史,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金茨堡说微观历史研究时所使用的资料,也可能就是一条脚注的素材。他本人即是在意大利一座小城中发现了一批宗教裁判所的审讯档案——数以千计的卷宗。在翻阅目录时,他偶然注意到一条记录,这条磨坊主的记录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抄下了该案的卷宗编号,准备日后深入研究。然而这一“日后”竟跨越了七年。七年后,他才重新返回该地查阅这份材料。最终,从发现线索到《奶酪与蛆虫》的出版,又经历了七年的历程。整个过程,从最初的灵光乍现到最终的文本问世,跨越了十四年之久。
在我看来,微观史更像是一种“文学性的考古”,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联结与重构。历史学家就像侦探一样,需从一地碎瓦、一页传单、一个失语者的口供中,顺着线索的蛛丝马迹追踪下去。当然可能最后得不到任何所希望的结果,但是也可能会发现被尘埃掩盖的历史。这种工作考验的既非机械的记忆能力,也非单纯的资料占有能力,而是想象力、敏感性、深切的共情以及表达的能力。
微观史兴起的历史背景
要理解微观史的兴起,必须回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学术环境。在《历史的微声》一书里面,我画过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插图,金茨堡就深受葛兰西的影响。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长期遭墨索里尼政权囚禁。他的大部分理论贡献都是在狱中完成的,后被辑录为《狱中札记》。他在《狱中札记》中提出,要关注民众的日常经验与文化生活。这种思想启发了包括金茨堡在内的一批历史学家,他们开始重视底层个体的历史,其中就有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汤普森(E. P. Thompson)等著名历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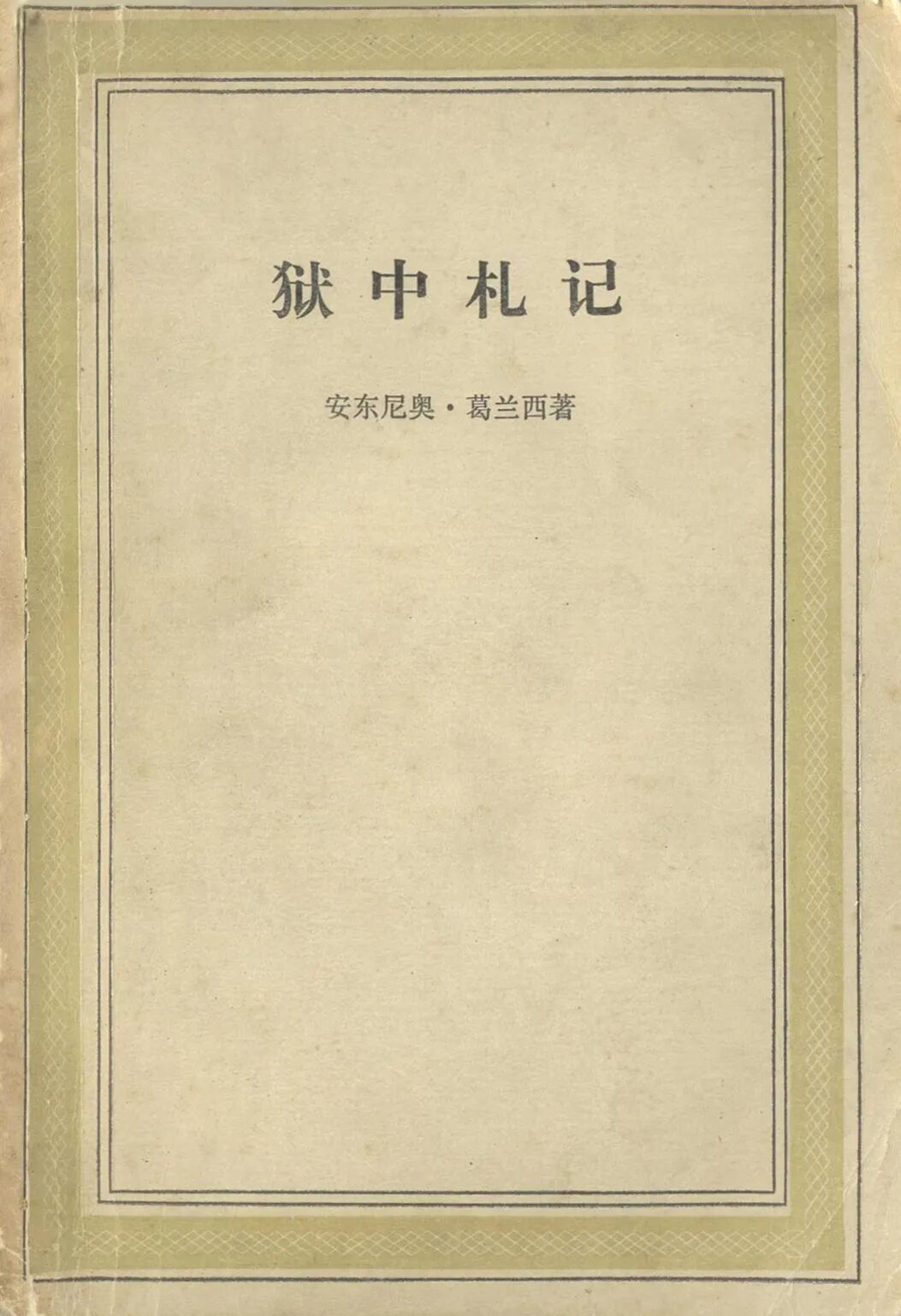
安东尼奥·葛兰西著《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球范围内爆发了激进的社会运动,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浪潮……正如电影《阿甘正传》所折射出的那个时代,激情与不安、理想与混乱并存。全球激进的政治氛围进一步刺激了对宏大叙事的反思和对微观视角的兴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历史研究也经历了剧烈的转向。一九六六年创办的《历史笔记》(Quaderni Storici)杂志,为这些志同道合的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标志着微观史学术共同体的诞生。而金茨堡的学术轨迹,也在这些背景下逐步成形。《线索与痕迹》正是对其多年思考的集中呈现。这本二〇〇六年出版的论文集,不同于叙述完整故事的《奶酪与蛆虫》,汇集了他几十年来的学术演讲与专题论文。这些论文跨越不同主题,却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历史学如何在解构主义与后现代怀疑主义中坚守“求真”的立场?
这就引出了金茨堡最重要的论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海登·怀特的《元史学》(Metahistory)被视为后现代历史观的经典之作。怀特提出,历史写作与文学共享叙事结构(如浪漫剧、悲剧、喜剧、讽刺剧)和修辞手法(如隐喻、讽喻),本质上都是一种语言建构,其真实性受限于书写者的主观视角。这一后现代立场消解了传统历史学追求客观真相的根基,将历史推向“文学化”陷阱,甚至模糊了历史与虚构的边界。
怀特的观点对金茨堡而言,是一个对客观历史的巨大挑战。这意味着历史作为“真理”的可能性遭到了根本怀疑。正是在这种理论对抗中,金茨堡发出了他的回应——强调“线索式推理”、痕迹的阅读能力,即便历史是间接的、片段的、不完整的,但仍然可以通过微观的观察与严密的逻辑分析,逼近某种“事实”的核心。这种主张既是对怀特的回应,也是一种试图在后现代语境中保留“真相”可能性的努力。
金茨堡的回应不是简单的客观主义。他并不否认历史有主观性,而是强调:即使主观不可避免,历史学仍需追求可靠性与责任感。他始终坚持,历史研究应建立在具体材料、经验分析和批判理性之上。这正是《线索与痕迹》这本书想要传达的核心精神——在怀疑与解构的时代,坚持以微观细节的观察、蛛丝马迹的追寻,探索人类经验的可能真相。
金茨堡的解决路径:细节对抗宏大叙事
面对海登·怀特的挑战,金茨堡选择以另一种路径回答:他回到细节、回到档案,尤其是那些看似琐碎甚至荒诞的宗教裁判所记录,在一个又一个被忽略的场景中寻找历史的真相。他认为,细节并不是宏大叙事的敌人,而是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路径。“魔鬼藏在细节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这句西方谚语,正是他的方法论的生动注脚。
在金茨堡的代表作《奶酪与蛆虫》中,一个叫梅诺基奥的磨坊主成为主角。在那个以宗教为权威的时代,他说宇宙是像奶酪一样,从中生成的蛆虫,即众生。他是一介平民,仅仅是在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中留下了一些关于上帝与世界本源的“异端”言论,但正是这些言论——夹杂着民间传说、异端信仰和自己的思辨——让我们得以进入十六世纪一个底层农民的精神世界。
从金茨堡开始,微观史学倡导者不断挖掘“非主流”的资料,如宗教裁判所的笔录、税务登记、遗嘱、口述资料等。过去学界普遍轻视这些材料,认为它们内容庞杂、无甚价值。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历史学家开始大量使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作为研究资料。这些档案记录极为严谨,连受审者的每个表情、每声叹息都被详细记载。通过分析这些“被扭曲的记录”,反而能还原底层民众的真实思想。
当然,金茨堡也知道,使用这些资料充满了挑战。例如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往往充满“预设性”:审讯官的问题有明确导向,被审问者不得不在某些语言框架内表达自己。这时候,历史学家的工作就不是简单地“再现”,而是对文本本身进行剖析,在歧义、偏差、字里行间寻找真实。金茨堡正是通过这种“与文本搏斗”的方式,把碎片化、断裂化的档案还原为一段段鲜活的生活经验。
比如,金茨堡的另一部作品《夜间的战斗》中描述了意大利农民到野地去与魔鬼搏斗的仪式行为,用秸秆高粱和魔鬼鏖战,曾被宗教裁判所定义为“巫术”。但金茨堡却敏锐地发现,这种“夜间战斗”其实是一种农业社会对丰收的祈祷,是民间仪式的一部分。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叫“本南丹蒂”,其中文意思就是善行者,善行者做善事。金茨堡没有接受宗教法庭对问题的预设,而是穿透这些权力结构所建构的叙述,去寻找其背后真实的信仰系统。在这种意义上,金茨堡并不否认历史存在建构成分,但他坚信细节拥有自证的力量——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仍能在建构中看见现实的痕迹。就像瑞那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所说的,这是“历史的微声”(small voices of history),是被国家和精英话语遮蔽的历史真实。
在过去,我们常用“黑暗的中世纪”来形容欧洲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常常让人联想到草菅人命、思想禁锢、宗教裁判所的残酷。然而,当我读了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之后,我发觉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磨坊主的罪名确实荒谬——仅仅是因为他质疑了上帝创造一切,但裁判所的审判却异常严肃和详细。更让我震撼的是,梅诺基奥第一次被捕后曾写信忏悔,因身体状况不佳而获释,但被限定活动范围,还得穿上带有标志的衣服。几年后他再度因言获罪,这一次,教会甚至为他指定了律师。这个律师并非只是一味附和教会的“傀儡”,而是认真地为他做无罪辩护。整整十几年的审讯,几千页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一个宗教机构在运作时的严密与理性——虽然这种“理性”仍然服务于压制异端的体制。
这一切让人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黑暗”。如果我们以为中世纪的残酷是非理性的野蛮,那么二十世纪以“文明”之名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与种族屠杀又如何解释?
我自己非常认同这种以细节为突破口的研究方式。我的著作中也常常充满了琐碎的描述:人物衣着、天气变化、街道细节、家庭矛盾,甚至是一句话中语气的转折。有些读者可能不习惯,觉得太“碎”,太“慢”,影响了对“重大问题”的把握。但我始终相信,一旦我们用细节去观察,原本看似“理所当然”的历史进程便变得充满偶然性和复杂性。
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一九八五年,我陪一位美国学者考察大渡河太平天国遗迹。我们调查了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为什么在大渡河覆灭,这似乎就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他的小妾临盆生子,他为此庆祝,于是把已渡过去的士兵召回,这一耽搁,刚好赶上当晚大雨倾盆,河水暴涨,因而无法渡河。数日后清军前后夹击,全军于紫打地覆没。
历史不是必然的,不是决定论的剧本。在我看来,历史是由无数细节与偶然构成的复杂拼图。我们习惯于从“结果”倒推“原因”,寻找所谓的规律、趋势与逻辑,但当我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那些被称为“必然”的路径,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
微观史与“真相”的张力
《线索与痕迹》第十章所讨论的《锡安长老会纪要》,则提供了一个关于历史如何被虚构与利用的范例。这本在二十世纪被广泛用于反犹宣传的小册子,表面上是一群犹太长老秘密会议的纪要,实则是十九世纪法国一部讽刺拿破仑三世的小说《地狱对话录》的改编和伪造。俄国人通过篡改人物名称(如将“马基雅维利”替换为“犹太长老”),将其包装成“犹太人密谋统治世界”的阴谋论手册。
金茨堡并未因文本的虚构性而否定其历史价值,反而追踪其文献脉络,不仅还原了伪造的过程,还通过对纸张、水印、批注等细节的分析,揭示了它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历史文件”,揭露反犹主义如何利用文字嫁接建构仇恨叙事。
即便是伪造的文本,也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其篡改过程、传播机制与被接受的历史语境,揭示时代的思潮、政治的动向、权力的操作。正如我在研究川渝“袍哥”历史时发现的那样,袍哥自己声称我们的起源是来自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立堂所留下的《金台山实录》。他们从海里打捞上来一个密封的铁盒子,里面就有这本书。《金台山实录》经过整理印行后被称为《海底》,就成为了袍哥他们的经典文献。尽管这个故事极可能是虚构的,但我仍然是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对这个文献进行分析,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起源和郑成功拉在一起?虚构的文本本身就反映出他们组织建构合法性的诉求——通过神圣化的起源,来强化凝聚力和权威。
我究竟是如何践行“通过线索、痕迹去发现历史”的理念,也反映在我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记事(1912-1928)》中。其中第十二章,我专门讨论了“大事件与小人物”的关系,而这恰恰是我在历史研究中所坚持的一种观察方式:通过微小之处,寻找时代的回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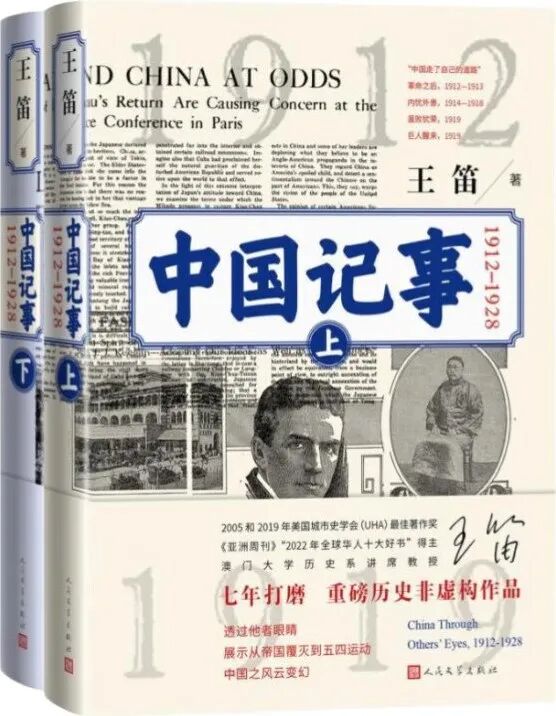
王笛著《中国记事(1912-1928)》,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版
我想大家对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应该不陌生。“巴黎和会四巨头”即英、美、法、意四国的领导人,日本实际上是“第五巨头”。这些巨头在这次和会中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左右着会议进程。当时的世界舆论几乎都聚焦在这些政治领袖身上,比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他们构成了国际政治舞台的核心。
然而,我在第十二章中关注的,并不是这些高高在上的人物,而是一位可能无人知晓的普通中国人。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一位署名“K. P. Wang”的读者向《纽约时报》投去了一封信。我们都知道,《纽约时报》当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他选择在这样的平台上发声,可谓用心良苦。
在信中,王先生表达了对“巴黎和会”的不满和愤怒。他指出,这次和会实际上摧毁了中国人对“新秩序”的信任,是列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妥协,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还质问美国:不是一直主张“门户开放”吗?可这次的决定却与这一政策背道而驰,甚至是对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严重背叛。的确,威尔逊虽然提出了许多理想主义的主张,但在巴黎和会上,这些最终以失败告终。更令人震撼的是,王先生在信中写道:“如果有一天,中国人不再坚持和平的传统,那不是我们的错,责任在强权而非中国。”他说:“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也是不可战胜的。”这封信用词铿锵,情感真挚,我相信当时看到这封信的美国读者一定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愤怒和坚定。
这封信发表后,引起了不少回应。其中,一位名叫毕格洛(Poultney Bigelow)的亲日派美国人于五月十二日写了一封回信,反驳王先生。他以“黄种人的解放者”论调为日本辩护,提出“日本不是魔鬼,是相当温和的”,“控制了山东是为了拯救中国”等奇谈怪论。对此,王先生在五月十六日又写了一封信,坚决驳斥了毕格洛的论调。他指出,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只有侵略与灾难,中国人从未认可所谓的日本“文明”统治。他更明确地指出:“亚洲门罗主义”本质上是对中国主权的否定,不可能被中国人接受。
之后,更有第三方人士弗雷德里克·麦考米克(Frederick McCormick)以讽刺的笔法声援王先生,说王先生的信“惊醒了这位住在纽约哈得孙河畔玛尔登(Malden-on-Hudson)同胞的睡梦”,还调侃他“大笔如椽,声如洪钟”(Its pen is big, and its voice is anything but low)。
我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故事?因为这正是我所坚持的历史观:真正的历史,不仅发生在领袖的谈判桌前,更存在于无数普通人留下的文字、情绪和痕迹之中。王先生的声音也许只是众多历史碎片中的一片,但它所映照出的民族情绪与历史记忆,却穿越了一个世纪,至今仍令人震撼。
这封信不仅还原了被宏大叙事湮没的个体抗争,更揭示出五四运动全球语境中的民间外交维度:当顾维钧等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时,普通华人正通过跨国媒体力争表达中国的诉求。我们可以看见历史背后的真实情感,理解事件的复杂结构,也意识到:哪怕只是一个人、一段文字,也可能在关键时刻点亮整个时代的良知。
结合金茨堡“线索”和“痕迹”这两个关键词,我想引用《中国记事(1912—1928)》里的话,作为结束语。所谓的线索,就是“顺着那些蛛丝马迹,可能引导我们到那不为人知甚至波澜壮阔的历史。好像宫崎骏电影《千与千寻》中的那个小孩,一旦通过了那个神秘的隧道,一个未知的奇幻世界立刻展现在眼前”。
至于说到痕迹,“雪泥鸿爪,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来过,就难免不留下任何的痕迹。但问题在于,99.99%的这些踪迹,最后被历史的尘埃掩盖了。所以我在想,我们历史学家有时候也得靠运气吃饭。一旦发现了前辈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我们就要进行奋力的追踪,但是这些痕迹很少能把我们引导到历史的真相。我们的追踪,经常是原地踏步。因为更多的时候,那些宏大叙事把普通的个体都通通掩埋了”。
这就是通过线索、通过痕迹发现历史真相的意义所在:不是去重复已被验证的宏大叙述,而是在历史的细缝中,重新发现那些被遗忘却真实存在的生命与真理。
(本文首发于《书城》2025年9月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